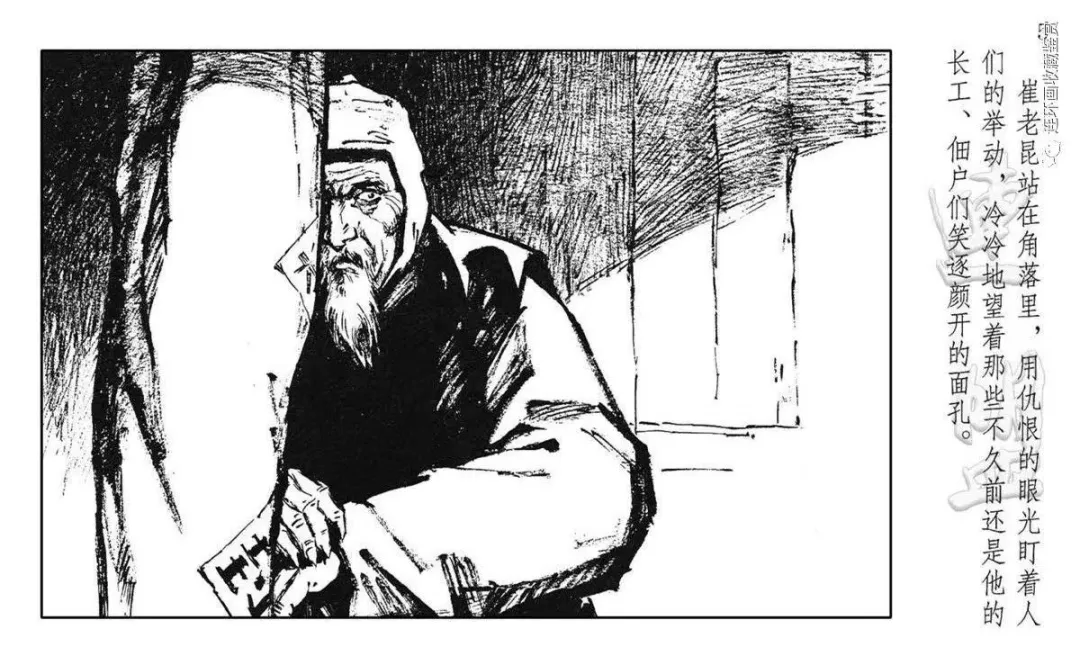
孙正源在其一系列文章中,大多是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幌子,向那些其口中“反对改革开放”的“极左”进行攻击的。然而如果有心人能够对他的论点论据进行一系列评判,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实践,宣称‘历史上所有社会都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名义上的公有制。”理论层面上,孙正清运用形式逻辑替代辩证思维,割裂制度与实践的关系,进而以西方唯心主义历史观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
为了验证我的定论可靠性,下面就把他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曝光,并进行系统的驳斥:
一
孙正清说:认真审视辛宇的论点就可以发现,他说的“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道路、根本制度来说,必须严格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因为两者是根本对立的”,是非常错误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在根本制度上有区别甚至对立,但怎么发展方向和道路也可能有对立?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是实现现代化科技化,难道社会主义可以与这个方向完全对立起来。
我的驳斥:
孙正清利用片面的思维逻辑对辛宇观点所进行的批判,其逻辑是非常荒谬的。
辛宇强调两种社会制度在根本方向、道路和制度上的对立,这一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本质差异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生产关系的本质区别,二者存在着根本制度对立。
因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服务于资本增殖,结果会导致贫富分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如:中国的"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物质与精神协调,这是二者从发展方向上的差异。
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扩张完成原始积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因此,二者在道路选择上的道德准则截然不同。
而孙正清的论调是,两种制度在发展方向上不应对立,他的这一论调有意忽略掉了现代化的阶级属性。因为资本主义的科技发展受资本逻辑支配,如AI技术加剧失业危机、医疗技术被垄断资本控制。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局限性根本就不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日而语。
反观中国,中国将科技自主创新用于惠及民生。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依托自主研发的大数据,实现了利用“健康码”精准防控的目标,从而极大地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而北斗系统、高铁技术等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并且通过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帮助农民拓宽销售渠道、建设生态文明等实践,致力于让科技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
通过对比可知,孙正清故意将生产力的技术特征(科技化)与生产关系的阶级属性混为一谈。这种张冠李戴式的叙事,在本质上存在着严重的理论误区。事实是,社会主义虽然同样追求科技进步,但拒绝异化为资本奴役的工具。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不仅充满血腥殖民,而且至今依然利用金融和军事霸权收割第三世界国家。反观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提供新型全球化方案,二者在方向上怎么可以相同呢?
因此,辛宇的观点在本质上是正确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上存在对立,在生产力发展层面可以借鉴对方的技术成果,但绝不能对资本主义不分良莠的照单全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恰恰证明了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的前提下,能够创造出更优越的现代化路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正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生动体现。
二
孙正清说:所有上市公司都应该是集体所有制的,属于公有制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有证监会,有国资委,有市场监管局等一众部门进行管理。现在,上市公司的高管都快成了资本家的代名词,到底该由谁来解释清楚,什么样的企业属于公有制什么样的属于私有制,天天拿公有制私有制说事的人,有没有人能说清楚?
我的驳斥:
1、上市公司所有制多样,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因接受证监会的监管就认定为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公有制。因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分标准是控制权归属,而并非是否受国家管理。
证监会监管的目的是规范市场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而非是将企业“公有制化”。美国也有证监会,但你能因此认定苹果、微软是公有制企业吗?
2、孙正清所谓的“上市公司高管成为资本家代名词”的说辞,其实是不准确的。正常情况下,现代企业制度的规则是,资本与管理相互分离。
高管未必是股东,但也可以通过股权激励或高薪与资本利益绑定。这种现象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企业均存在。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服务于股东利益最大化(如追求股价、分红),事实上体现了资本的意志。与此所不同的是,虽然个别国企高管有可能会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结果背离了公有制“全民所有”的初衷,但这属于监管和治理问题,而非所有制本质问题。
3、如何明确区分公有制与私有制?
虽然国企混改中所形成的混合所有制引入了民营资本,或民营公司引入国有资本,答案依然是看实际控制权。
即:根据控股权判断主导性质。
国有或集体资本控股(持股≥50%或具有实际控制权),性质是公有制。公司是私人或民营资本控股,则是私有制。公有制企业理论上应服务公共利益(如保障就业、战略行业),利润归国家或集体。私有制企业以股东利益为核心,利润归私人所有者。二者的企业目标和分配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4、而孙正清源通过偷换概念来混淆“监管”与“所有制”之间的区别,试图将国家对市场的监管等同于公有制。其实孙正源所设的逻辑陷阱,无非是想推销他所编织出来的所谓“受国家监管=公有制”的概念。若此逻辑成立,全球所有受监管的私营企业都可被强行归类为“公有制”,然而这种归类法明显违背了经济学常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明确区分出不同所有制,并赋予各自合法地位。若强行将所有企业“公有制化”(或反向操作“全盘私有化”),都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颠覆。
孙正清通过错误的前提,推论出荒诞不经的结论,如果结合他一直对公有制的恶意表述,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论调隐含着不可告人的意图。他想通过混淆所有制的性质,来泛化公有制的概念(把所有企业都说成“公有制”),从而模糊掉真正的公有制(国企、集体企业)与私有制的界限, 把私营企业伪装成公有制,表面上看,似乎在“创新”公有制概念,实则暗推全盘私有化。 这是一种先混淆概念,再彻底颠覆的策略,类似苏联解体前某些理论家鼓吹“全民所有制就是无主所有制”,最终为为他在中国推进“全盘私有化”来铺路,以实现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性质的图谋。
三
孙正清说:私有制社会出现什么现象,要看政府能发挥什么作用,和法制是否健全。人类历史上万年,基本上是私有制社会。哪怕中间几十年出现过一些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从根本上说仍然属于私有制社会的社会形态,没办法实现公有制。
我的驳斥:
孙正清的这一论述存在多重理论漏洞与事实误判。
资本主义政府之所以是私有制,其本质是资产阶级的“总管家”,其作用受制于资本逻辑。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用7000亿美元救市,却最终流向华尔街而非普通民众。
而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并非“名义上的公有制”。以中国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而宪法保障并非口头上的。
中国国企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比例从2012年的5%~15%提升至2023年的30%,资产总额从2012年的104.1万亿元增至2023年的300万亿元,直接用于社保、医疗、教育,反哺民生领域。而且国有企业承担着80%以上重大基础设施与核心技术攻关。
另外,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存权,防止了印度和拉美的那种因土地兼并,致使农民失地的现象。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制,抑制了房地产和资本的无序扩张。中国国有经济控制关键行业(如: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等),因而可以防止资本垄断和系统性危机。
这说明,社会主义政府代表人民行使了生产资料管理权。如果无视这些结构性差异,仅以“政府作用”模糊阶级本质,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诡辩。
因此孙正清所谓的:“哪怕中间几十年出现过一些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从根本上说仍然属于私有制社会的社会形态,没办法实现公有制。”之论,明显是在闭着眼睛说瞎话。
孙正清论点的逻辑谬误性体现在偷换概念上,他将“政府监管有效性”等同于“私有制必然性”,忽视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与资本的本质区别。政府在公有制经济中是“所有者代表”而非“中立仲裁者”。
而孙正清以个别腐败案例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如同因银行行长贪污,就否定储户存款所有权一样,这种逻辑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
孙正清的论述本质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变种。其错误根源在于,孙正清用资产阶级经济学框架强行解读社会主义,用形式逻辑替代辩证思维,从而割裂了制度与实践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而以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否定非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其结论必然与事实相悖。
四
孙正清说:这些论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人,从来不会认同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因此对于改制以后的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国有参股但不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国企既不控股也不参股的股份制企业,很自然地让人归类为私营企业。这种不由自主的联想和让人联想,是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们一贯的套路,目的当然是为了反对国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这样的下三烂被他们说成是维护公有制,除了反对改革开放还能作何解释!
我的驳斥:
1、国有不控股只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其所有制性质并不随国有资本参股比例的增减而发生本质变化。
根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综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国发〔2015〕54号)的表述,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性质由所有制结构决定,而非单一股东的持股比例。只要企业包含国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无论国有资本占比高低,均属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就是说,企业整体性质不变,它既不是国有,也不是单纯的私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因国有资本比例高低而改变其“混合”属性,仅体现国有资本在其中的权重差异。
即:国有参股企业的公有制性质不因持股比例变化而改变企业整体性质,但国有资本占比的变化会影响其在公有制经济中的权重。企业整体仍属于混合所有制,公有制成分的存在是混合所有制的一部分。
单纯就国有参股不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来讲,虽然公有制经济成分依然存在,但主导地位已让位于控股方。
2、国企既不控股也不参股的股份制企业,因完全不含公有制资本成分,所以不属于公有制经济,其性质由实际控制权决定,通常归类为非公有制企业。
3、从以上解析不难看出,孙正源的所谓:“这些论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人,从来不会认同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之言属于无的放矢栽赃,因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需从全国公有资产总量和国有经济控制力综合判断。
4、孙正清将“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国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对立,暗示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人必然反对改革。通过动机揣测,将支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直接等同于“反对改革开放”。如此这般,缺乏起码的事实依据,这是典型的“先歪曲对方论点后,再进行攻击”的稻草人式的诡辩术。
5、孙正源通过偷换概念,将“混合所有制企业”简单等同于“公有制企业”,故意忽略中国经济体制的复杂性。
因此,孙正清口中“这些论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人”视角着眼于全国公有资产总量和国有经济控制力,这难道有错吗?莫非只有鼓吹“全盘私有化”,才能成为孙正源口中的“政治正确”?
总结
孙正源的一系列言论在理论、政策和实践层面均存在严重谬误,其核心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发展方向”上不应对立,仅承认“制度”差异。
2、鼓吹荒谬的“上市公司=公有制”论,即所谓的,因上市公司受证监会等监管,故应全部视为公有制。
3、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实践,宣称“历史上所有社会都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名义上的公有制”。
4、将“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国企改革”对立,污蔑支持公有制的人“反对国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孙正清通过混淆概念(如“监管=公有制”)为私有化制造理论依据。 其逻辑实则是“监管泛公有制化”,以此企图模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界限,为变相私有化铺路。试图将国企市场化改革推向“全盘私有化”的不归路。孙正清的论点本质是新自由主义伪装下的意识形态攻势。因此,必须警惕此类打着“改革”旗号、实则颠覆基本经济制度的错误言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